目录
快速导航-
特别推荐 | 清流
特别推荐 | 清流
-
特别推荐 | 人散后,一钩新月天如水
特别推荐 | 人散后,一钩新月天如水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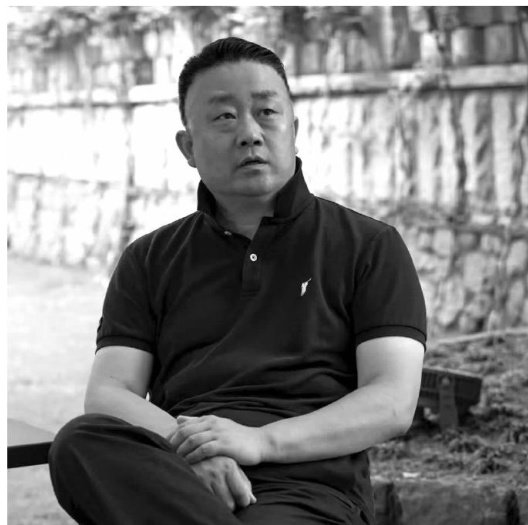
特约专栏 | 不时不食
特约专栏 | 不时不食
-
作家视野 | 我的一九七八
作家视野 | 我的一九七八
-
作家视野 | 稻城记
作家视野 | 稻城记
-

作家视野 | 绿皮车上的凉山人(外一篇)
作家视野 | 绿皮车上的凉山人(外一篇)
-
作家视野 | 顺应自然的牧羊人
作家视野 | 顺应自然的牧羊人
-
别具只眼 | 典中自有汉语美
别具只眼 | 典中自有汉语美
-
别具只眼 | 河边走走
别具只眼 | 河边走走
-
别具只眼 | 开往春天的列车
别具只眼 | 开往春天的列车
-
别具只眼 | 蒙山沂水新红嫂
别具只眼 | 蒙山沂水新红嫂
-
性情写作 | 无边的城乡
性情写作 | 无边的城乡
-
性情写作 | 流过时间的河
性情写作 | 流过时间的河
-
性情写作 | 劳作之余
性情写作 | 劳作之余
-
海天片羽 | 铜铃摇碎的暮霞
海天片羽 | 铜铃摇碎的暮霞
-
海天片羽 | 菜事二三
海天片羽 | 菜事二三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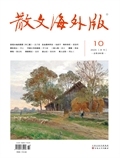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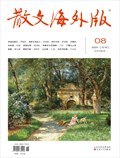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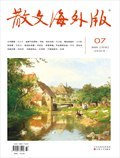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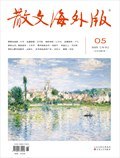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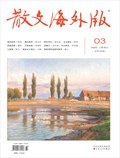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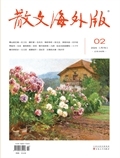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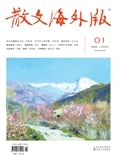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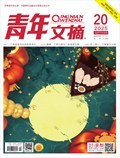




 登录
登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