目录
快速导航-

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 | 论语言接触及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作用
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 | 论语言接触及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作用
-
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 | 民族性与革命性的双重叙事:延安时期马加的文学实践与共同体意识建构
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 | 民族性与革命性的双重叙事:延安时期马加的文学实践与共同体意识建构
-
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 | “两路”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哲学意蕴及实践路径
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 | “两路”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哲学意蕴及实践路径
-
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 | 符号·情感·行为: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文化认同维度
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 | 符号·情感·行为: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文化认同维度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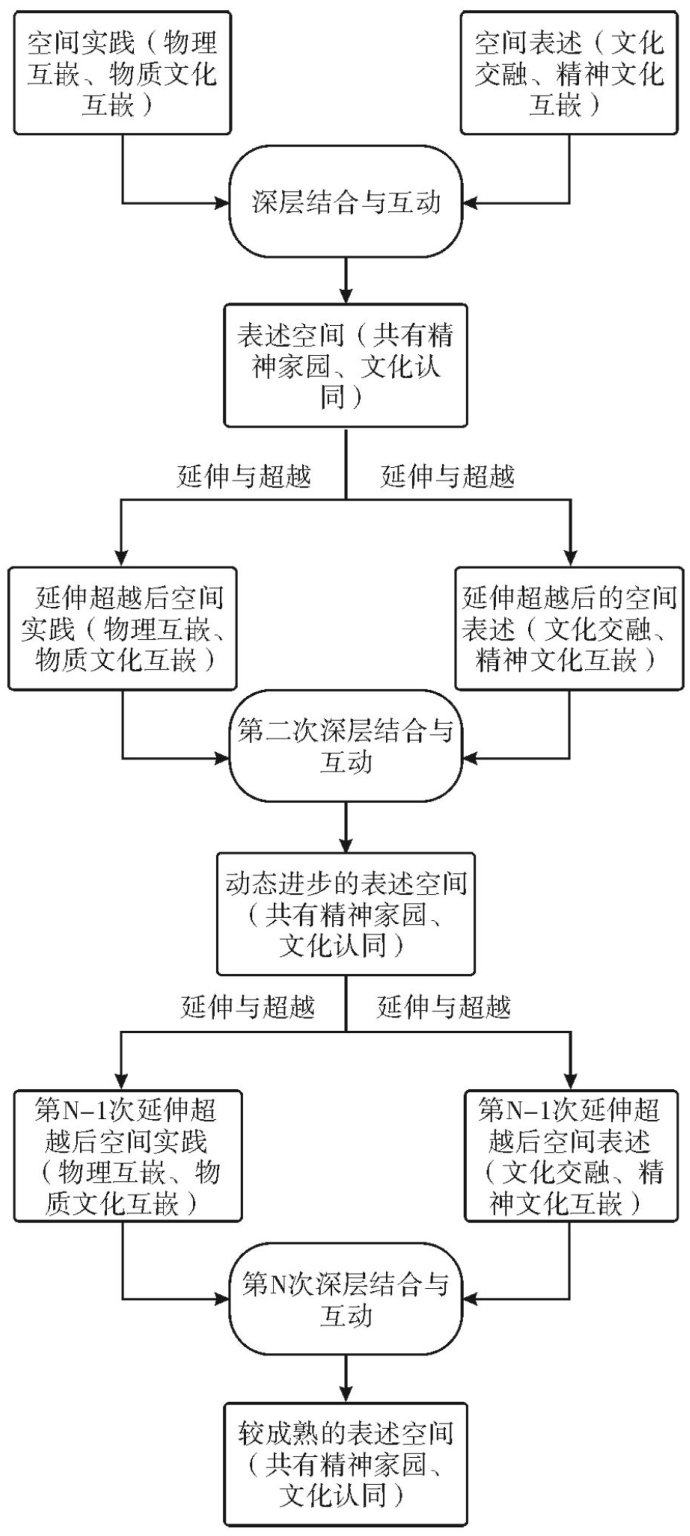
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 |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路径探析
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 |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路径探析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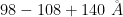
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 |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助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机理、价值与路径
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 |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助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机理、价值与路径
-
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 | 新型城镇化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
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 | 新型城镇化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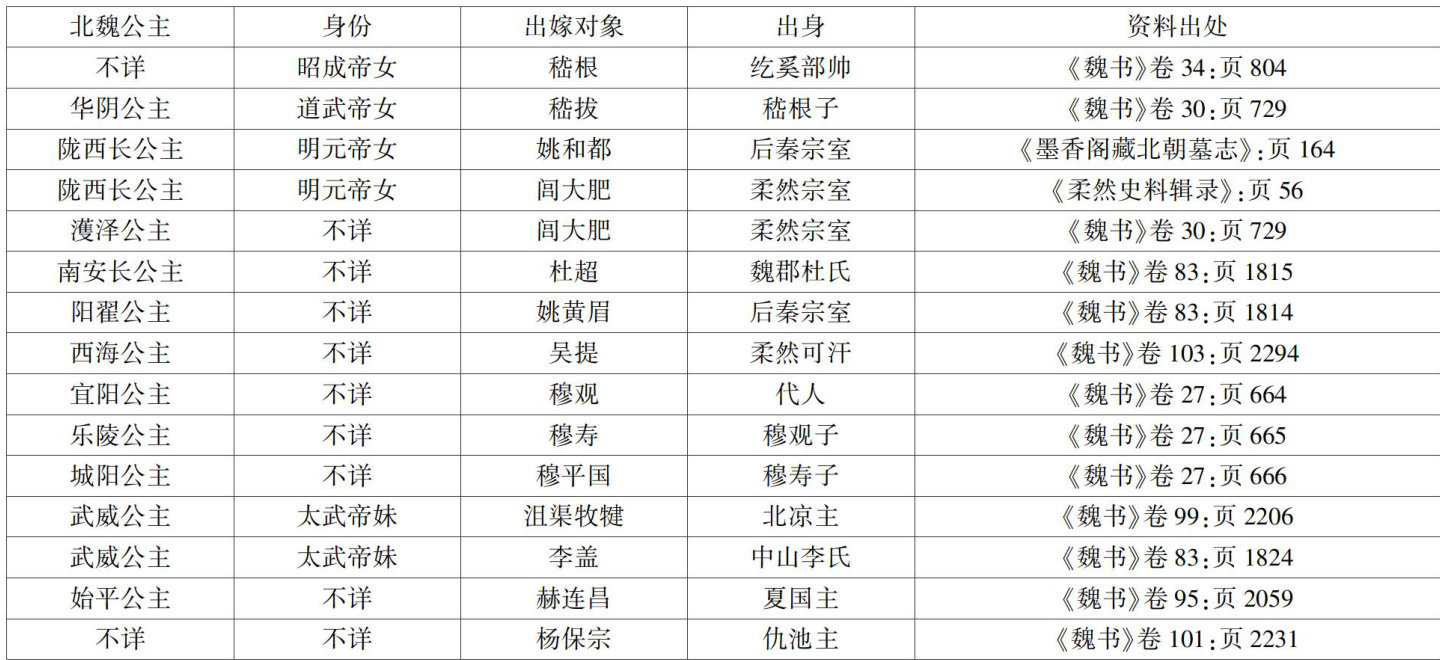
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 | 从北朝公主通婚看各民族血脉相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成
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 | 从北朝公主通婚看各民族血脉相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成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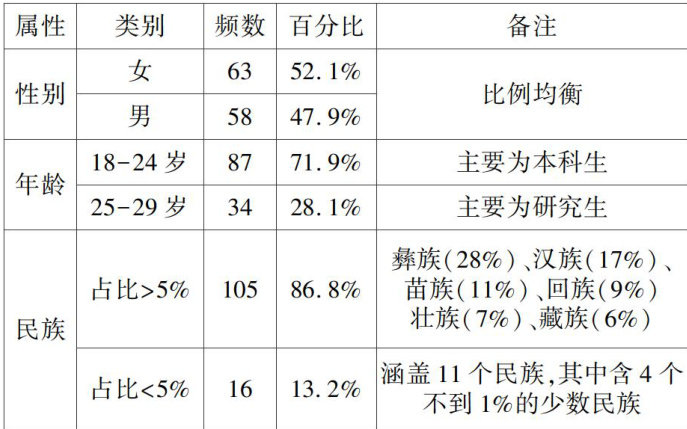
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 | 民族高校学生国家通用语言认同的现实样态、阶段特点与动力机制
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 | 民族高校学生国家通用语言认同的现实样态、阶段特点与动力机制
-
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 | 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:实践探索、模式归纳与法治进路
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 | 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:实践探索、模式归纳与法治进路
-
民族学/人类学研究 | 文化转型人类学田野研究的方法论启示
民族学/人类学研究 | 文化转型人类学田野研究的方法论启示
-
民族学/人类学研究 | 从教育民族志凝视世界
民族学/人类学研究 | 从教育民族志凝视世界
-
边疆学、边疆治理与国家安全研究 | 抗战时期边疆大学的边疆研究
边疆学、边疆治理与国家安全研究 | 抗战时期边疆大学的边疆研究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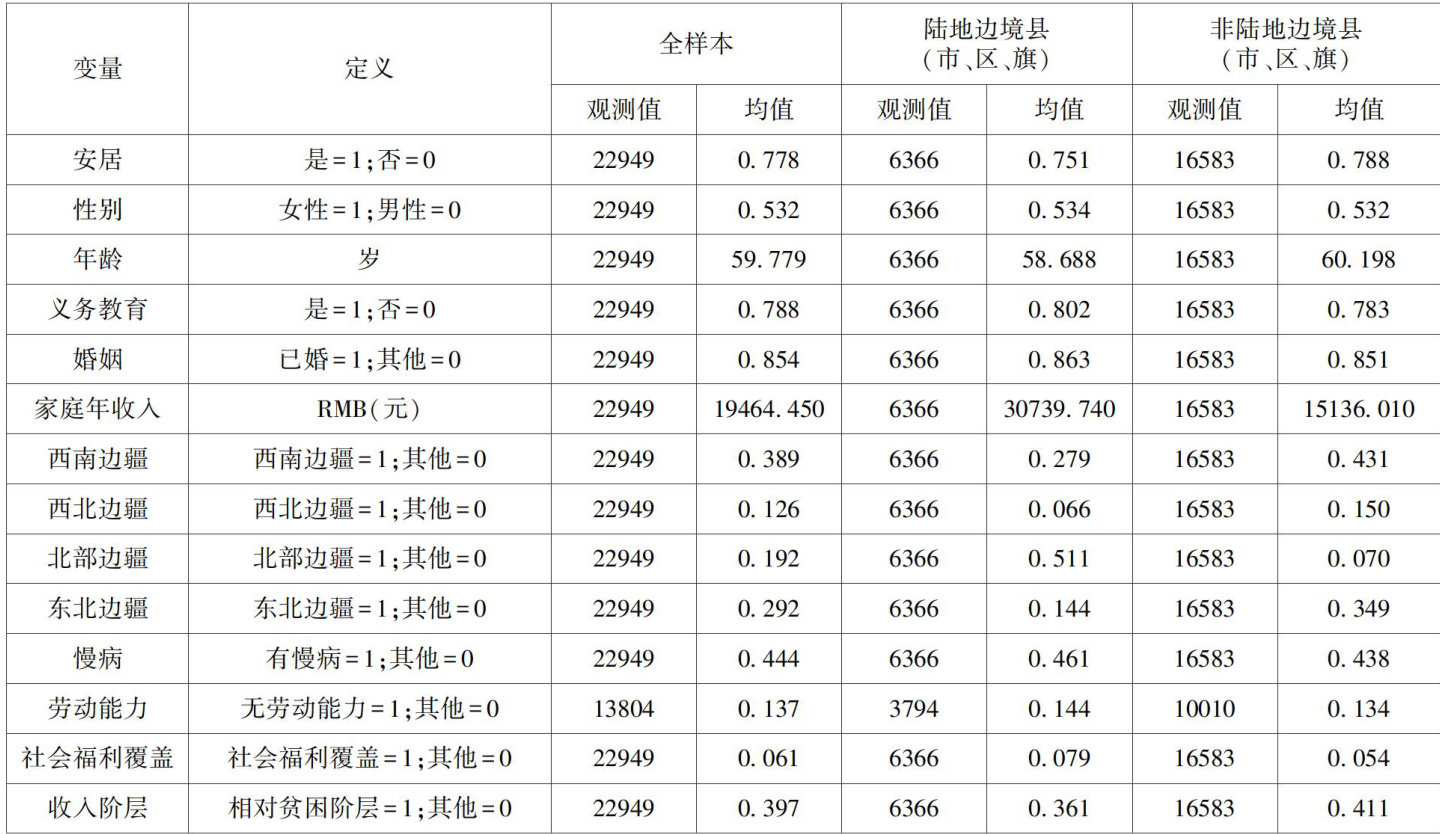
边疆学、边疆治理与国家安全研究 | 兴边富民行动的安居效果及其影响机制
边疆学、边疆治理与国家安全研究 | 兴边富民行动的安居效果及其影响机制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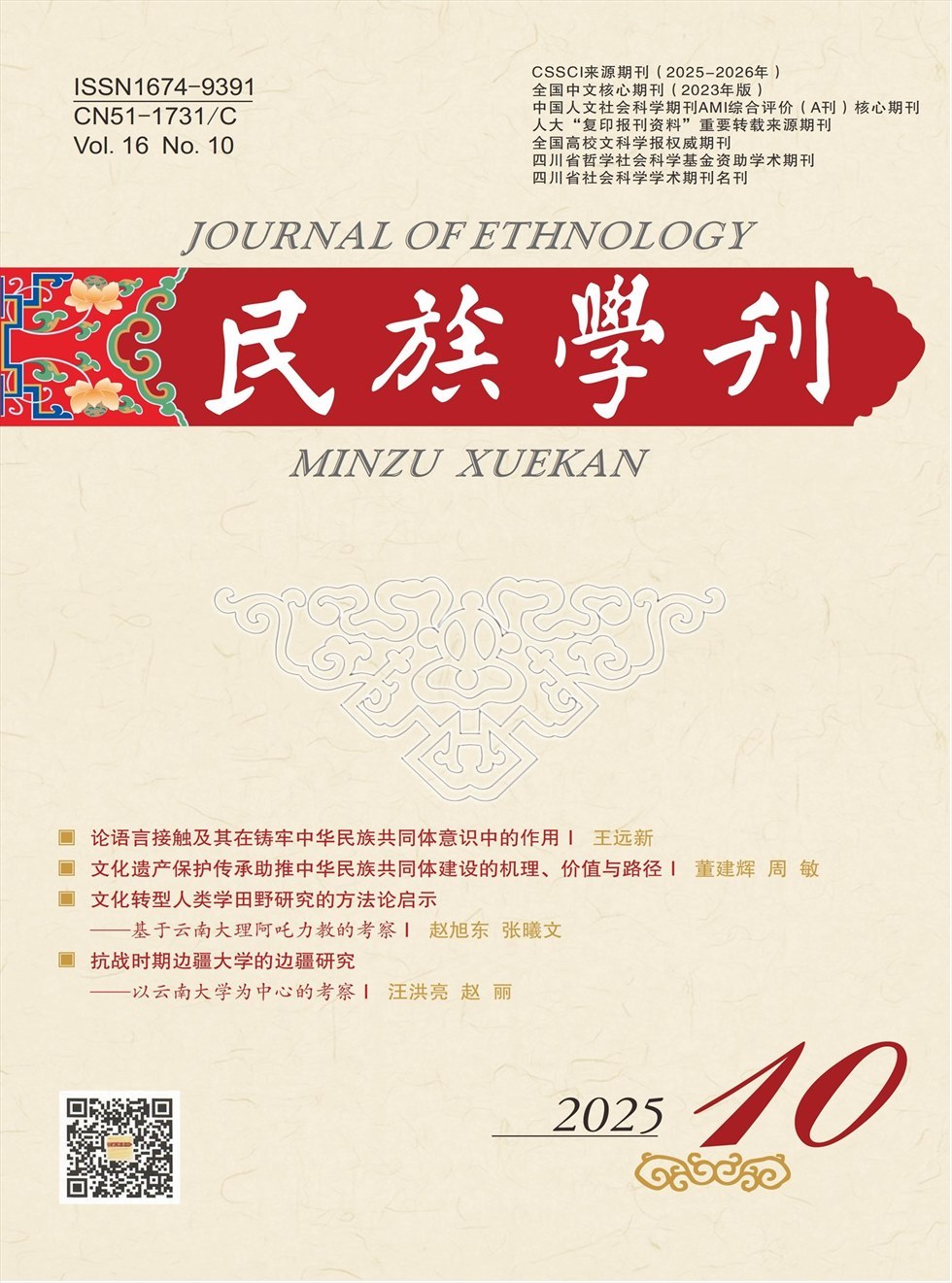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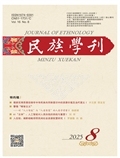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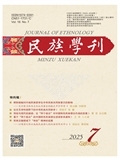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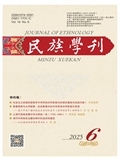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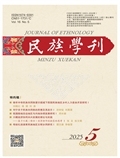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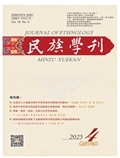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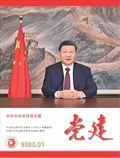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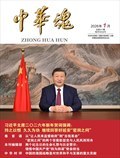


 登录
登录